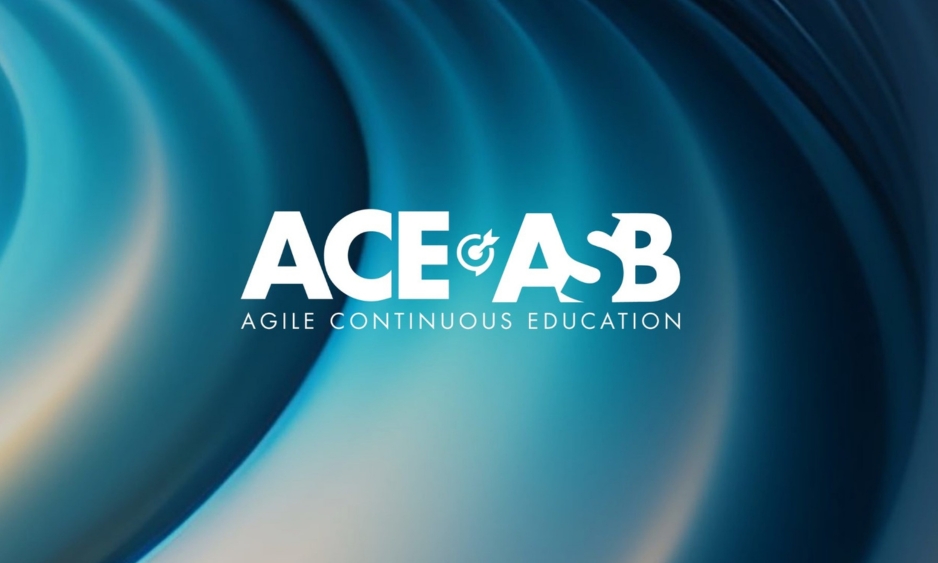曾经弹无虚发的神枪手,如今不敢再拔枪;曾经温和的丈夫,如今因小事而暴怒;曾经活力的妻子,如今沉默如冰……
导致他们“失常”的,可能是一次重大事故、职场霸凌,或长期的精神高压造成的心理创伤。
身体的伤,看得见;心里的伤,隐蔽、难以察觉,不仅会击垮当事人,更会像涟漪般扩散至家庭。我们该如何识别这些信号?政府、公司组织又该如何给予协助,降低员工遭受心理创伤的风险?
在职场上,无论是站在前线的军警、消防拯救人员、人道救援成员、重症监护人员、社会工作者、宗教中特定职位的工作者甚至是办公室里的白领、工厂里的蓝领,都有可能因为工作期间经历或见证极度紧张或恐怖事件,如自然灾害、暴力事件、严重事故或攻击(遭遇性侵、霸凌),而留下心理创伤,甚至严重至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(PTSD,又名创伤后压力症候群)。
然而,需要被看见和治愈的,不仅仅是受创伤的当事人,家属或照顾者亦是隐形受害者。
亚洲商学院(Asia School of Business)组织行为学副教授王怡人和研究团队的后设分析(Meta-Analysis)研究显示,职场上的心理创伤不仅会冲击当事人,连带可能影响其家庭的心理健康,首当其冲的往往就是最亲密的伴侣、子女或者照顾者。
照顾者痛苦“共情”
这项研究项目始于王怡人在美国就读博士班期间,初衷是了解美国军人家庭的压力状况。过程中也发现无论是面对生死一线的军警与医护人员,甚至是在办公室里遭受霸凌、性骚扰的白领员工,他们所经历的心理创伤,都会间接的传递给伴侣及家庭。
研究也进一步发现,即使伴侣或照顾者并未亲身经历或目睹有关的重大冲击场面(如战场上的生死离别,急诊室里惊心动魄的抢救,在会议室里被上司羞辱),但他们会因为“共情”与“照护”受创伤的当事人(“我爱的人正遭受某种不合理、不公平或痛苦的对待”),心理健康所受的危害程度与痛苦指数,可能不亚于甚至等同于遭受创伤的当事人。
王怡人指出,这存在两种可能:
●亲密关系发生变化:
当一个人经历创伤后,其行为模式会发生根本性改变,可能出现易怒、警惕、逃避或麻木等症状。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氛围、沟通模式和亲密关系质量,间接损害伴侣和家人的心理健康。
●同情心疲劳:
伴侣在不断倾听、安抚和提供情感支持的过程中,会持续消耗自己的同情心和心理资源。这种过度付出虽然有助于受创者的康复,却也让伴侣自身处于高度脆弱的状态,最终可能导致其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。
这并非危言耸听。
双威医疗中心临床心理治疗师魏爱灵受询时透露,“很多人会因为他们感到焦虑、忧郁或沮丧而来求医。但在谈话中我们慢慢发现,其实一部分的原因是和他们的家庭,或者另一半可能经历了一些事,导致他们的情绪也受到影响。”
不同角色的扮演
企业、国家、领导者、主管在职场创伤扮演的角色:
◎组织/企业:
当职场成为创伤的源头,企业无法置身事外,这不仅是出于人道考量及照顾员工,更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息息相关。
王怡人指出,员工心理健康与企业实则同舟共济,忽视员工心理健康,对企业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损耗。“如果一个优秀的员工因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留任意愿或工作表现,企业将不得不投入更多成本重新招聘和培训。”
因此,投资于员工的心理健康,等同于投资于企业的稳定性与未来。
投资心理健康=投资未来
她主张,若工作环境可能面临高度的职业灾害和职业创伤风险,企业或组织领导层需建立强大的安全网络,例如招聘时列出工作特征让应征者考量、提供训练,确保前线工作者更有意识地应对潜在挑战;其次,定期评估员工心理健康状况,营造心理安全的环境和沟通机制,让员工感受到被倾听、被重视。
除了关怀员工心理健康需求,亦可将关怀延伸至员工的家属,其他措施包括推动如弹性工时、弹性工作地点、主办心理健康讲座等措施以提升认知、破除对心理创伤的污名化等。
◎领导人与主管:
王怡人分享一起本地案例:一名警消人员在某次任务后出现严重的恐惧和反抗行为,其妻子经过长时间的陪伴和倾听才得知,他当天目睹了极具冲击性的现场。由于缺乏同事、主管和组织层面的及时心理支持与干预,该警消人员出现了PTSD反应,长期处于极度不安状态,严重影响工作表现。
她强调,主管和领导者应接受系统性培训,学会倾听、介入并提供支持,而非将员工的求助视为个案或特殊情况。
构建心理安全感文化
魏爱灵补充,主管和领导者可以构建心理安全感的职场文化,鼓励员工自由表达意见,不必担心因犯错或坦诚困境而遭受指责或影响职业发展。
她观察到,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营造心理安全环境的重要性,值得注意的是,必须学会平衡。
她解释,一些人会误认为过度强调同情和帮助他人会影响工作效率,“心理安全感的目标并非牺牲工作表现,而是促进更有效沟通,增强团队成员间的同理心和相互理解。”
疫后至今,她接获不少企业邀请,为员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、提供压力应对指导甚至处理心理问题。她认为这表明企业对员工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正在逐步提升。例如,她所在双威医疗中心就为员工提供免费的心理健康相关支持,甚至惠及员工家属。
◎政府:
王怡人表示,相较于生理层面的职业灾害和意外风险评估,包括大马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,在心理健康方面的法规仍相对不健全或缺乏,这导致员工心理健康的照护,目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意愿。
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或许可倡议政府立法明确企业在保障员工心理健康方面的责任,搭配监督机制及合理适当的资源分配,以强化对职场心理健康的重视。
自行采取自下而上
“如果国家未能自上而下地推动,企业很容易就会认为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‘不关我的事’或是觉得既然政府没有强制要求,自己‘何必操劳这些’。因此,若能由政府率先制定法规并有效推行,提升公民意识,无疑是最有效的方式。”
倘若法规的制定速度落后于社会风气和需求,她认为民众可采取自下而上的草根行动,积极倡导和推动从而影响企业,促使其关注并改善员工的心理健康。
小心保护你的心
魏爱灵表示,在高压工作环境中,工作者需采取多方面措施保护心理健康。
首先,维护个人私生活。这意味着确保工作时间不会侵占个人时间。她表示,下班后如果只是感到疲惫,只想看电视、吃饭睡觉,那么心理健康很难得到维持。因为高压会导致身体产生压力荷尔蒙,长期累积若得不到释放,将逐渐影响生理健康。因此,需要通过一些减压方式如运动、培养个人爱好来释放这些荷尔蒙。
其次,建立支持系统不可或缺。这意味着拥有可以沟通、倾诉的对象,甚至在需要时能获得实际帮助。例如,当工作压力过大无法照顾孩子时,能有人伸出援手。这些看似小事,却对心理健康助益良多。
先麻木再爆发
对于曾遭遇心理创伤甚至PTSD患者,魏爱灵指出,当局者迷,比较难以自我察觉,“有时候创伤并非即时显现,你可能会先麻木一段时间,之后才爆发反应。你会疑惑为何几个月前的事情现在才有如此大的反应。”
正是这种延迟性,导致当事人极难自我察觉。此时,身边的“局外人”如家人或朋友的观察和一句简单的提醒,例如“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”或“什么事情影响到你”,或许就能如同警钟般起到关键的提醒作用。
此外,她也指出,时间并不能自行治愈心理创伤,特别是PTSD。例如,因为工作环境有毒或与老板冲突而遭受心理创伤并更换工作的人,即便在新环境面对“小事”,仍可能感觉“回到了之前的状况”,这正是因为他们的“情绪容纳之窗”变窄,必须加以拓宽,有的人接受药物治疗、有的选择心理治疗,也有一些人选择什么都不做。
【自·救·指·南】
●关于当事人:
打破沉默,进行沟通并寻求帮助。魏爱灵表示,沟通是重要的预防方式,在事情恶化前,家人之间坦诚地交流彼此的感受和观察,能为可能到来的风暴铺好缓冲带。此外,家庭以外的社群支持,可在当事人孤立无援时,提供情感慰藉和实际帮助。
●关于照顾者:
“你要照顾别人之前,要先把自已也先照顾好 。”王怡人指出,照顾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,感到疲惫、焦虑甚至急躁,都是正常的身心反应。她建议照顾者要正视“同情心疲劳”,允许自己有疲倦和急躁的时候,并适度调低“我必须为他负责”的道德枷锁,给自己喘息的空间。因为研究也显示,一个耗竭的照顾者,无法为任何人提供有效的支持。
一点就炸或彻底躺平
有没有发现,在现实生活中,遇到事情发生时,有的人“一点就炸”,却也有的人“彻底躺平”,这或许与性格无关,而是与“情绪容纳之窗”(Window of Tolerance)变窄有关。
魏爱灵指出,每个人的情绪波动都存在“情绪容纳之窗”,其宽度受个性、成长背景和经历影响。
当心理健康且富有弹性时,即使面对挑战,情绪也能原有的“窗口”内(例如30公分)波动,意味着我们能有效管理情绪,正常生活。例如感到不开心但不至于逃避,生气但不至于过度争执或陷入焦虑、躺平,这都属于健康的范围,能正常工作和学习。
情绪容忍度降低
然而,当一个人经历创伤或长期压力会使大脑自动收窄这个“情绪容纳之窗”(例如收窄至20公分),当事人对情绪波动的容忍度随之降低,情绪稍有超出便可能出现两种极端反应:
(1)反应过激:
持续高度警觉和亢奋,表现为焦虑、情绪失控,甚至与人争执;
(2)反应过低:
表现出极度的麻木、抽离和回避。
例如,创伤前能处理5项工作任务,创伤后面对同样任务量可能感到“不行了”,随即陷入争吵或逃避,影响工作表现。此时就要重视自己的心理,或积极向外要求救援
Originally published by Nanyang Siang Pau.